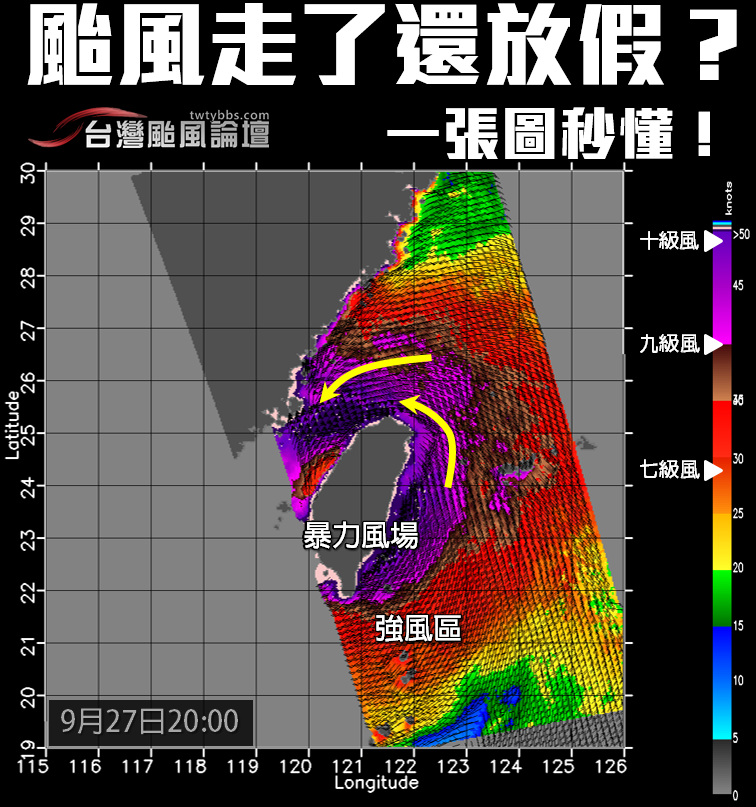八重山物語(二):移民共譜的族群記憶
2016/09/21 15:15:43 阿潑

在異鄉,試著打造、還原故鄉的一切,有多麼難。 圖/記錄片《海的彼端》歷史照片
分享
2003年,謝安琪第一次到石垣島做田野時,一個關於「八重山的台灣人」的系列報導,正在《八重山每日新聞》連載。出身台灣的謝安琪,自然被這個題目吸引,仔細閱讀,才知道原來八重山群島與台灣千絲萬縷的關係。她曾經想過要以此展開自己的研究,但後來怕路線衝突,於是轉而研究八重山民俗與台灣關係和異同。即使如此,日後,她逢人便會說:「松田先生是我的恩人,給我很多幫助。」
謝安琪提到的「松田先生」,就是執筆者松田良孝。這個連載於2004年集結成冊,出版成書,名為《八重山的台灣人》(這本書繁體中文版於2012年由行人出版),此書順著歷史脈絡,有系統地說明1930年代,為了躲避徵兵,又或為了求取生存,遷移到八重山群島的台灣人故事。
在這本書的前言中,松田良孝提到自己自2000年開始這個採訪,甚至從石垣島搭船到台灣,直奔雲林,為了探訪某位台灣移民的故鄉,好描摹他所說的故事。這個連載以「我們都是台灣來的」為標題,他說:「八個字構成的這個標題,是答案,也是提問」。
從日本殖民時代至今,八重山的台灣人在八重山打造出生活的基礎,超越了國家、國籍帶來的變動,偶爾也煩惱「我是誰」這樣的問題。
在同屬日本殖民地的那個時代,移動並不需要經過太多程序,就像東北或九州的日本人來到台灣開墾一樣,他們搭個船也就能往八重山群島而去,儘管當時這些島嶼人少、偏遠且荒蕪,但對台灣人來說,不啻為一個可以開墾的新天地。許多台灣人或跟著台中石岡的林發來此種鳳梨,加入大同拓殖株式會社,或是靠著關係而來。

在同屬日本殖民地的那個時代,許多台灣人或跟著台中石岡的林發(圖)來到八重山開墾,加入大同拓殖株式會社。 圖/聯合報系圖庫
分享
八月底,我們在石垣島市區閒晃,由著松田良孝與謝安琪引領我們參觀。松田良孝會突然手往前指,說:「這家是台灣人後代。」或者進了熱鬧的市場,走到一家鳳梨酥攤前,說這也是台灣人後代。又或者坐進咖啡店,等待點餐的時候,他們往櫃檯指去:「這是林發大兒子的媳婦。」
若非他們指引,或是店門前面有明顯的台灣文化字樣,我們這些人走在石垣島,其實也無法分辨誰是台灣來的,誰又不是。
當然,這些人都在松田良孝的連載裡出現,尚且不論林發這個地方上最有名的台灣人,那個不起眼的鳳梨酥攤的老闆娘,就是《八重山的台灣人》第一章開頭的那個「芳澤」家族的媳婦,也是2000年松田良孝直奔台灣雲林探訪的故事起點。為了避免兒子被徵召上戰場,這家人先是乘船到了西表島礦區,再來石垣島,於是當這老闆娘簡單說出家族經歷時,眾人立刻啊啊啊地想起了書裡的內容。
腦中宛如有個八重山台灣人系譜與地圖的松田良孝,就跟這群移民一樣,也不屬於這塊土地,一九六九年出生於日本琦玉縣的松田良孝,在北海道讀大學,一九九一年畢業後,即在當地當起記者,兩年後轉赴石垣島,繼續記者之路。
聊起何以從日本最北端,往最南的邊境移動的理由時,他提到了一本書——灰谷健次郎所寫的《太陽之子》,「因為讀了這本書,我對南方小島心生嚮往。」確實,這個島在日本影視作品中,時常以海灘、熱帶風情為人所知,像是《琉璃之島》、《海灘男孩》,或是《HERO》最後飾演雨宮舞子的松隆子拜訪被放逐到小島的久利生公平,都以這裡為背景,在在彰顯樂觀、希望的氣氛,畫面明亮。
但《太陽之子》卻是一本悲哀的兒童文學,以移住神戶的沖繩孩子為主角,描述戰爭對沖繩的影響,及其對沖繩的追尋。但當松田良孝來到沖繩,甚至是沖繩旁邊的小島時,卻又捲入另一種追尋——關於台灣人的——他首先注意到這個理應屬於日本的地區,竟然有一群人說著他聽不懂的話,存在著一種陌生的語言。

松田良孝(右)腦中宛如有個八重山台灣人系譜與地圖,一路抽絲剝繭,完整耙梳筆中人物的歷史記憶。圖為松田良孝與玉木玉代阿嬤。 圖/作者提供
分享
當時除了一些學術資料,幾乎沒有什麼關於八重山台灣人的相關資料。起步有點困難。「幸運的是,那些年,石垣市政府很想要吸引台灣旅客,於是非常支持這個計畫。」松田良孝說,書寫這系列佔盡天時地利人和,包含老人們雖日漸凋零,但也因年紀大了無所畏懼,不擔心歧視,而放膽地訴說一切,「如果早些年,他們還在職場打拚時,可能就不會說了。」
「第二代的青壯年,沒辦法,幾乎不想說。」他表示,因為過去台灣人在當地被歧視,青壯年在職場上本就有壓力,更不想因為自己台灣人的身分再被欺負或排擠,於是不願表露身分也不想談這件事。
關於台灣人被當地人排擠、歧視的故事,在他書裡也有不少著墨,像是開墾初期,台灣移民就屢遭排擠,特別因是水牛的蓄產力而生的衝突。八重山本無水牛,台灣移民將水牛移入這些地區後,引起極大的爭議,因為一頭水牛能開墾的面積是人力的許多倍,當地人害怕土地遲早都被台灣人佔領去。當時林發是這麼回應的:
雖然是台灣人,但也是天皇陛下之子,現在因為實施日本國民南進政策,政府以台灣為南進基地,從本土過去的人就不用說了,八重山也有很多人去到台灣,台灣人、沖繩人都是自己的同胞…。
然而,終戰之後,台灣不再是日本屬地,沖繩乃至於八重山群島自然也由美軍托管,這個時候,台灣與八重山不僅不再是「同胞」,八重山/沖繩與日本之間也不是,但台灣人更確確實實是被以紅線畫出來,在這個辛苦耕耘十多年的土地上,成為「他者」。「台灣人滾出去!」的吼聲再次響起。
我住在石垣島上,沒有給任何人帶來麻煩,來到這個島後,我非常非常努力在做事,也真的沒有帶給別人麻煩,我明明沒有做壞事,為什麼會這樣?
松田良孝採訪的第一代移民這麼感嘆。

歷史浪潮的拍打下,國籍轉換削弱台灣移民的權利,這些人不停地在「同胞」、「他者」與「我是誰」之間游走。 圖/記錄片《海的彼端》歷史照片
分享
因為國籍轉換的問題,台灣移民的權利薄弱,要獲得基本的受教權也很辛苦,若要到日本讀大學,首先面臨的就是國籍的問題。除此之外,在當地就學的移民二代,也因遭到歧視,於是不再願意說母語。這些第二代長成後,遇到戀愛婚嫁的問題,仍然因台灣人的身分遭到否定拒絕,甚至必須私奔解決。
相較於第二代、第三代青壯年,第一代比較願意談論往事,但也不見得順遂,松田良孝表示,老人則因記憶曖昧,讓他必須屢屢查證,像是一個老人說自己不能上學,讓他很是懷疑:「不是規定都要接受教育?」實際走訪台灣、查閱資料,才知老人的家鄉確實受教率很低,許多人沒有上學。
這種種問題,在松田良孝的筆下完整耙梳,最後像是有了個比較正向的答案。族群界線似乎消弭了,我卻認為,或許只是從大眾的眼裡消失。
耗費時間精力完成這個專題的松田良孝,對台灣與八重山關係的追尋,並沒有因此停下來。他接連寫了《台灣疎開:「琉球難民」的一年十一個月》及《與那國台灣往来記:在「國境」生活的人們》,皆和台灣相關。
他的最新作品,是本名叫《インターフォン(內線電話)》的小說,主題亦是八重山的台灣人。在完成這些題目後,他來到台灣學中文,想要進一步了解、探訪在台灣讀書生活的石垣島年輕人,想知道他們是否產生變化。他想做的,無非是不斷嘗試連結兩個地區。
這是松田良孝的遷移,他帶著問題,尋找解答。
雖然沖繩和台灣之間存在國界,但我覺得國界不是很重要,重要的是每個人的生命與生活。儘管在異鄉會有衝突,但如何圓滿解決與和平共處,才是最珍貴的。我想傳達的,是人跟人之間的連結與感情。

八重山的老人們雖日漸凋零,但也因年紀大了無所畏懼,不擔心歧視,而放膽地訴說一切過往的故事。圖為玉木玉代阿嬤。 圖/作者提供
分享
離開石垣島的前一天,我們跟著松田良孝到了班那(バンナ)山,登上展望台,從高處俯瞰名藏灣與名藏地區,這是當初台灣人開墾所在。
名藏位在於茂登岳和嵩田山留下土砂所堆積的平原地帶,屬名藏川流域,自早就是稻米耕種的古村落。琉球王朝時代,名藏人口約有七百人,但1771年的明河大海嘯讓人口迅速減少。1891年出身於德島的中川虎之助,曾帶人來這個地區開辦糖業,但不久便失敗。1930年代由台灣移民取代開墾。戰後,宮古島與沖繩本島的移民填入這塊地區,台灣人被迫離開這個地區。
松田良孝往下東指西指,向我們解釋那是台灣人的學校,那是芒果溫室,另一處三合院樣貌的宅邸則是台灣人的家。我們看到的田園景色,是台灣人闢下的。說起了書中曾提過的種種故事,種種的衝突,松田良孝深有所感。
站在這個高處,往右手邊看,同樣能看到嵩田。嵩田是個被風雨削過的小丘陵,原本被森林覆蓋,很難想像可以成為耕地,但1920年代,有人試著種茶,於是有著茶山的稱號。
1935年,台灣人創立的大同拓殖株式會社在這個地區開墾,闢出鳳梨田與罐頭工廠,然太平洋戰爭末期,工廠被日軍接收,公司也被關閉。台灣人只好移居到カート這個地區,從頭再起。戰後,有一段時間,是鳳梨榮景,更多台灣人往這裡移居、工作。直至1970年代,趨於衰落,但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。

台灣移民將水牛移入八重山後,引起極大的爭議,因為一頭水牛能開墾的面積是人力的許多倍,當地人害怕土地遲早都被台灣人佔領去。如今,水牛卻成為八重山醒目的風景。 圖/作者提供
分享
我們隨著松田良孝下山,往剛剛看到的「三合院」前進。
說起「三合院」,台灣出身的我們腦海都有個既定的樣貌,但眼前所見的「三合院」,不過就是排成ㄇ字形的三個灰色水泥房,眾人莫不碎碎唸起來:「難怪在山上怎麼也看不到哪裡有三合院。」
然大門一推開,我們的疑惑碎唸頓時平息,內裡陳設確實與我們熟悉的台灣宅邸相同,先是見到神明桌、觀音與王母娘娘相,再來就是祖先牌位,大廳牆壁上掛著裡先人的照片,明顯是第一代移民的父祖輩。
再往兩旁走去,先是三合院主屋會有的房室,再來就是廚房,那帶著綠色防蝿網的櫥櫃,以及鐵製大碗罩,確實是台灣鄉間的必備。另一個小屋,則置有磚頭砌成、升火用的大爐灶,農產收穫、成串香蕉則放在地上,頭一抬,是農民慣穿的白色汗衫掉在竹竿上。分明就是台灣。
「這家姓黃,後來歸化日本籍改成淺野。」松田良孝說,老人家去世後,後代也不在這裡居住,但每天仍會來開啟窗門,讓空氣流通,保養這個父祖留下來的房子。在如今的石垣島,這是最接近台灣特色的建築。我突然可以理解,在異鄉,試著打造、還原故鄉的一切,有多麼難,於是對這其實並非三合院的三合院的建成,有些感悟。
松田良孝在我們到來之前,曾寫過這家人的故事:就在我們到訪的前一個月,尼伯特摧毀台東後,往北走來到石垣島,聽到颱風消息的淺野文雄,急忙趕著採收麻竹葉。淺野文雄是移民第二代,從母親那裡學得了包粽子的方法,而這麻竹葉,就是粽子的材料。他們試著以竹子裝潢自己的家裡,也試著以竹子維繫父母所保留著故土的記憶。
離開這座三合院後,我不免也反省到,所謂的「保留、情感或記憶」,終究是我們作為台灣人的視角與情懷,當我們試著要在這個土地尋找自己熟悉的味道與記憶時,往往忘記這不過就是歷史,而這些人都活在現實裡,他們有自己的生活和記憶,不必向誰證明他本來是誰,或者他是誰。
而我們所該做的,不過就是認識這段歷史,而後,理解彼此。

透過八重山的台灣人的故事,我們認識這段歷史,而後,理解彼此。 圖/記錄片《海的彼端》歷史照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