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林芳儀 國立臺灣文學館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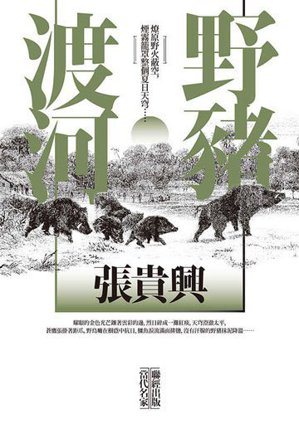
作者:張貴興
出版社:聯經出版
出版時間:2018年9月3日
《野豬渡河》中寫到:「人類必須心靈感應草木蟲獸,對著野地釋放每一根筋脈,讓自己的血肉流濬天地,讓自己和野豬合為一體,野豬就無所遁形了。」由此,人與人之間的生存戰,和為生存四處衝撞的野豬,並無分別。
從懷鄉到望鄉,鄉愁的淡化與轉化
張貴興面對故鄉婆羅洲,隨著時間流逝,逐漸產生不同的心境。從年輕時到現在,張貴興的作品從雨林間的情慾,到雨林間的拓墾,再到雨林間的掠奪,批判力道逐漸加重。張貴興對此種說法並不否認:「我年輕時比較浪漫一點,理想化一點,而最近的作品,批判性是多了一點,因為每次回到故鄉,看到馬來政府築起水壩,破壞原始森林,都會生起不滿,而當地人選擇默默承受。」張貴興生長在婆羅洲西北部的砂拉越(Sarawak),有著豐富的天然資源,他喟嘆的說:「馬來人是『西馬』的原住民,而不是『東馬』的,種族組成並不相同。1963 年馬來西亞獨立,新加坡原屬馬來西亞,1965 年也獨立出來,而砂拉越卻沒有,豐富的天然資源掌握在執政者馬來人手裡,當地原住民依然貧窮。」
張貴興把這份批判當成「自然而然」的事,種族間的掠奪,是張貴興小說中重要的母題。《野豬渡河》主要是批判軍國主義對東南亞的剝削,前一本長篇《猴杯》講述了中國人在婆羅洲開發的一個胡椒園,剝削當地的工人。他說:「我的批判是很輕的,帶著濃厚的感情,帶著我對砂拉越土地的一種熱愛。我用的是一種柔性的批判,並沒有直接提到砂拉越要獨立,只是透過文字,讓大家看到砂拉越有那麼多天然資源。」張貴興提及一些當地的歷史,以及當地人看待的方式,語調輕柔而堅毅,他的批判確實包裹在土地記憶裡,跟著語言慢慢長出來。
關於鄉愁逐漸淡化的原因,除了雙親過世,較少回故鄉,張貴興還給了一個特別的答案:Google Map。他經常透過街景圖去看家鄉的變化:「我住的地方是一個叫做羅東的小鎮,不是臺灣的羅東,人口大約幾千人,透過 Google Map,我才發現明明地方小,卻有很多以前沒去過的。Google 一段時間就會更新地圖,所以我每隔3、5年都會上去看看故鄉的變化。」由於資訊發達,不受時空阻隔,加上英國人的資料,以及 1990 年以後當地共產黨書寫的回憶錄,對於婆羅洲所發生的事,張貴興甚至比當地的親人更加了解,彷彿從未離開過。
因此,張貴興可以僅憑多年前對雨林的記憶,揉雜網路上、書本上關於當地的資訊,用想像去建構一座跨越時空、虛實交錯的雨林,過去的雨林、未來的雨林,地理的雨林、文學的雨林。離開了家鄉這麼多年,他依然心繫著婆羅洲,卻又不會太渴望「實際」見到,那淡淡的鄉愁,寄在現代文明所建構出的虛擬空間裡,再捏塑打磨一番,投影在他的小說當中。
從地理的雨林,走入虛構的雨林
沉寂了 10 幾年,張貴興終於再度推出長篇小說《野豬渡河》,寫作進行了 14 個月,並未作大幅改動,僅刪去 4、5 萬字較無相關的部分。前段期間,他忙於教學和家中事務,剩餘時間太過零碎,只偶爾寫些短篇,將日記當做寫作,保持書寫熱度。後來他開始構思長篇,真正著手寫書是在 2016 年退休後,終於有大量時間專注寫作。除了書寫 1940 年至 1945 年二戰期間的《野豬渡河》,張貴興同時構想了 1960 ~ 1970 年代、1990 ~ 2000 年代,以砂拉越不同時期歷史作為基礎的小說。他說:「10 幾年沒有產出,回想起來也感覺不可思議,現在是用一種贖罪的心情在寫,把應該寫的東西寫下來,彌補過去那一段時光。不過退休之後,思考也更圓熟,此時寫出來的必定更佳。」
張貴興寫作相當仰賴直覺,主要會選擇小說這個體裁呈現,係因小說較有挑戰性,可以天馬行空說一個故事,而散文「真實感」太重,如果不適度運用虛構,史料未載的空白處便難填上。張貴興的書寫,文學性重於歷史性,他說:「我寫的不是歷史,是小說。」在史料的縫隙中,他著力勾勒出各式人物的互動細節,吸食鴉片產生的幻覺,追捕動物乃至情慾交纏,其中流竄的各色暴力,種種史料讀不到的訊息,藉由虛構一一達成了。
張貴興的雨林,根植於地理空間,又取自歷史文獻,而童年在雨林生活的記憶,又帶領他重新想像一座沒有邊界的雨林,從不同族群眼中投射出的雨林。「我寫的不是地理上的婆羅洲,是文學的婆羅洲;不是地理上的雨林,是文學的雨林。」張貴興喜種樹,同時也拿起他的筆,種出了一片雨林。
從雨林到城市,原始和文明之間
19 歲赴臺至今的張貴興,面對萬年認同問題時,擺了擺手說:「我無所謂。」他提起幾次返回砂拉越,遭當地攤販誤認的經驗,1990 年被誤認為日本人,2003 年到2005 年則被視為韓國人,而 2013 年,卻又成了中國人。這一段「誤認史」正好對應了該國經濟起飛,觀光客湧入的時點。張貴興當趣談講著,順道帶入歷史思考,面對種種誤認,他不以為意。「我跟那些攤販說,我來自臺灣。」他會視情況切換臺灣人/馬來西亞華人/砂拉越人不同的自稱,還特別簡述了砂拉越華人普遍認同情況:「當地把臺灣人、中國人、當地華人分得很清楚。」即使對於身分認同並不在意,張貴興仍然特別關懷砂拉越族群處境。砂拉越總人口 270 萬人以上,華人 60 幾萬,馬來人 60 幾萬,其餘皆為當地原住民。他喟嘆說著:
「原住民人口超過一半,比華人、馬來人加起來更多,然而政治卻操控在外來者馬來人手裡,由馬來人統治。」比起自身族群認同,張貴興更加在乎的是原始土地的樣貌,以及族群壓迫。

張貴興童年老家正好靠近雨林,家中時常有動物造訪,舉凡大蜥蜴、老鷹、蟒蛇、猴子、穿山甲……等,因而和雨林動物關係相當密切,自然寫入小說中,並未刻意挪用作意象。《野豬渡河》裡的豬芭村確實存在,本來全是野豬,直到華人進駐,將一眾野豬驅逐,抑或圈養起來。「芭」在南洋叫「山芭」,意指荒僻、無人住的地方,後來改作「珠巴村」,村裡人少養豬,大部分都是華人聚落。一開始動物雖遭人類驅走,關係還是相當密切,他們依靠野豬過活,養豬賣豬,到如今益發「文明」,人與動物的依存度降低,面對「原始」的消逝,張貴興深深嘆息。
從砂拉越到臺灣,使張貴興感受到「原始」與「文明」的巨大分野。他記得剛到臺灣時,獨自步出師大宿舍,沿寬闊的和平東路一直走,不敢走小巷,就這樣邊走邊看,像鄉巴佬一樣。他自言:「環境差太多,剛開始不太習慣。以前我家靠近海,晚上睡覺可以聽到海浪聲,像催眠曲一樣,在臺北卻沒有聽到那樣的聲音。臺灣到處都是人,家鄉放眼望去都是大自然,蠻荒的東西,森林、河流、天空,晚上未被汙染的星星。」他用樸素的方式描繪著兩地差異,蠻荒這個詞,被他用得飽含感情。
「我是從那裡『逃』出來的,為了有更好的發展和前途。」張貴興並不諱言,他和許多當地年輕人一樣,盼望出走,體驗「文明」帶來的光亮。不過離開越久,他對砂拉越的感情反而益發濃厚,更加了解當地,更深感文明帶來的,不可逆的毀滅。
本文為國立臺灣文學館授權刊登於聯合新聞網「閱讀」頻道。經編輯摘錄,全文詳見《閱:文學》臺灣文學館通訊67期,未經同意,請勿轉載。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